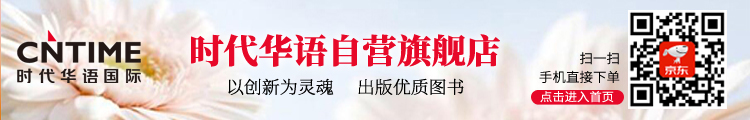序/徐家祯
去年一月底,我从中国休假回澳,家父、家母也与我同来澳大利亚定居。转眼竟然已经一年有零了。
我的居所位于阿德莱德东郊,在一片不高的丘陵之中,离市中心大约十七八公里之遥。这一地区原来是英国移民的聚居之地。他们从英国和欧洲大陆移植来了不少花木,再加上这一带正处于丘陵和平原的交界之处,云层遇到山丘上升变冷就凝结成雨雾,所以在以干燥著名的南澳州中,这儿却是难得的雨水充足地区。尤其是冬季,一周之中总有一半以上的日子是阴雨连绵、云雾缭绕。于是来自英国的居民大概联想起他们祖国苏格兰著名的Stirling,就以此命名这一地区。每年一到秋天,这儿山坡上、山谷里各种树叶都开始变色。有的红得像血,有的黄得像金,有的正在由绿转黄,有的却已变橙为褐,一时之间真是万紫千红、五彩缤纷。即使还没有搬到这儿来住之前,我已常在秋天驱车来此观赏红叶了。面对山丘上绚丽的秋景,我常常想起还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背过的一首唐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记得我念小学时家父曾教我背过不少古典诗词,但是我自小就表现出缺乏作诗的天资,所以随背随忘。然而奇怪的是,这首杜牧的小诗却成了我至今还没有忘记的不多的几首中的一首,可能说明我从来就对秋叶有所偏爱吧。其实这儿山上家家都种有茶花,从四五月开始,早开的茶花已在院中开放,直到十月、十一月,晚放的茶花还是满枝满丫的。虽说春天的色彩也很富丽,但我总更爱秋天的红叶,于是就把敝舍命为“红叶山庄”。
家父、家母初从车马喧嚣、人声嘈杂的大上海搬到远离闹市的山居与花虫草树做起伴来,确有些不太习惯。但是,几个月之后,他们渐渐找到了自己的新生活方式——家父除跟在上海时一样,平时不是伏案写诗、填词,就是与友人书信来往以外,现在添了一个活动:坐在屋外平台上,在终年浓绿成荫的六株大玉兰树下喝着茶看书报。家母近几年来在上海已经不再烧茶、煮饭,但是来了澳大利亚南部,觉得在这儿煮三餐饭菜不是难事,就“重操旧业”。中国的很多蔬菜和调味品在这儿无法买到,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呢。幸亏家母一向有把最普通的瓜豆蔬菜变成美味佳肴的本领,所以住的日子一长,又“技痒”起来,不但常做包子、饺子、馄饨、面饼,连粉蒸肉、素烧鹅、雪里蕻都做成功了。记得“文革”时期,一家四口靠我微薄的工资度日,每天的菜钱常常只是几毛钱而已,但家母还能变换花样,使全家人吃得津津有味。我的好友、现在住在墨尔本的倪兄那时常来便饭。他爱成语“活学活用”,有时能取得意外的效果。一次饭后发表了一鸣惊人的评论道:“真是妙手回春!”直到现在我们还常提起。不想三十年之后,家母竟会又在澳大利亚南部“妙手回春”!
除了做菜,家母又种起瓜豆来。她先将买来的干蚕豆种在草地的四周、花坛的边沿,山上气温较城里低四五摄氏度,豆子的成熟也比城里晚好几个星期,但是最后居然也收获了几十斤之多。除了嫩的采下炒食之外,老豆冰冻起来,随时取而食之,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吃完。
最有趣的是种南瓜。去年,我弄到十多粒加拿大种的南瓜子。可是因为园里种满花草,没有空地可种瓜果,于是家母就在花盆里种起南瓜来。她从我的工具房中找出大大小小十只花盆,小的只有直径三四寸,大的也不满一尺。我只当她是种着玩玩而已,没有当一回事。然而家母却认真浇水施肥,几周之后,居然每盆都抽出苗来。不久,瓜茎就长到尺许,然后就开了黄花。为了保证每朵雌花都能结果,家母就用一支棉签给每朵雌花人工授粉。结果,十盆南瓜每盆虽然都只有二三尺长的瓜藤,但每根茎上都结了南瓜,一共结了二十几个。这些小南瓜是供观赏用的,二十多个南瓜倒有十种不同的样子:有的皮色雪白光滑,只有小柿子大小;有的皮色碧绿,有西瓜似的花纹;有的像葫芦状;有的像一盏挂灯,有一圈翻起的荷叶边;有的像橙色的手雷,上边还长着高低不平的颗粒 ……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每天一早,家父、家母就去院子平台上赏瓜。如果发现有新开的雌花就给它授粉。然后就一个个研究南瓜的大小、式样、皮色,总有一两个小时可以消磨。
除了煮饭菜、种瓜豆,家母也开始看起书来。家母出身于世家,家教很严。我外公认为女孩子不用出去念书,进学校只能学会闹学*、交男友,不如在家请老师念。于是家母从来没有机会进入正式的学校学习。从五六岁开始,她跟家庭老师念读“四书”“五经”,还学过一些书画,直到十八岁嫁到徐家才中止学习。之后,当然是生儿育女,做个贤母良妻。虽说家里有男仆女用人可做帮手,但偌大一个家还是要家母来当。于是六十年来,不要说没有时间舞文弄墨,连看书看报的时间都不太有了。只有到了澳大利亚南部,因为家由我来当了,所以反倒有空看起书报来。我书架上有周作人、丰子恺、杨绛等人的散文,家母最爱看他们写的回忆性散文。除了他们生活的时代跟她的十分相似之外,他们的家庭背景也跟家母的十分相近,于是看了之后就激发共鸣,然后引起回忆。家母、家父常常边看边在院子里、饭桌上议论书中的内容或者自己过去经历过的事和认识的人,其中包括长辈、平辈、朋友、老师、医生、仆人,所谈论者大多早已作古了,一谈往往可以几个小时。我对家母说:“何不把这些人和事写下来呢?这不是跟周作人他们散文中所写的内容一样吗?”家父也从旁鼓动,我还答应为家母所写的散文做整理润色的工作。终于,家母动起笔来了。先从杭州一年四季的风俗习惯写起,再写到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倒也积累了不少篇。我边对母亲已经成篇的做整理、誊抄成文,边写了这篇小序,向能看到这组散文者介绍写作的背景,因为我觉得,了解这组散文的写作境地对理解这组散文的风格和特点是很重要的。
说到这组散文的特点,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文章中显示出来的平淡、自然、闲适的风格。这是我近十年来一直在自己的文章中尽力追求但自感一直未能真正达到的境地,而在帮助我母亲整理这组散文时,我却自觉基本达到了。周作人先生在《雨天的书·自序二》中说:
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
周作人的这段话道出了这组文章之所以能够平淡、自然、闲适的根本原因。我想,除了气质和年龄之外,最主要的可能就要算境地了。我近年来总想:为什么莫扎特、舒伯特能写出那么幽雅、舒坦的室内乐来?这不正是跟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那时的田园生活方式有关的吗?所以,如果不是在澳大利亚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我想,即使有了我母亲的高龄和气质两个条件,我也怀疑她能写出现在所写出的这组闲适散文来。当然,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人也同样可以满脑名利、满身铜臭,那么我们的这组文章就绝对不是为他们而写的!
这组散文中写的既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人物,又没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这儿记载的仅仅是近半个多世纪里生活在中国一个大家庭中的闺房小姐和家庭妇女眼睛里看出来的世界。但是正因为作者曾生活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又居住在相当特殊的家庭环境之中,所以她所写的平常事,从现在年轻人的角度来看就不很平常了。更何况这些小事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呢!即使对于现在生活在海外而以前来自同一个大故乡——中国的华人而言,能够通过这本书中所述的很多小事,来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从而更加感悟中国的将来的。正如唐朝大诗人王维所云: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中,我最佩服周作人。他1918年在《新青年》第五卷第六期上发表的题为《人的文学》的文章中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反对的是非人的文学。”后来,他又发表了《平民的文学》,把“人”的含义具体化为了“平民”。周作人主张要写“平凡人的平凡生活” (《谈龙集·竹林的故事》),他认为“生活里面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真正的大悲剧大喜剧,有之也多只是装腔作势、夸张扮演出来的,并不足以代表生活的全体”。(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直到晚年,他还重提自己的主张。在为上海《亦报》写的一篇只有四五百字的杂文《琐事难写》中,他说:
我们所要知道的还是平常人的平常事,有如邻人在院子里吃晚饭,走过时招呼一下,顺便一看那些小菜,那倒是很有兴味的。人与事是平常,其普遍性更大,若是写得诚实亲切,虽然原是甲与甲家的琐事,却也即是平民生活的片段,一样的值得注意。
现在,家母的这组文章,就是想写出周作人提倡的“邻人在院子里吃晚饭,走过时招呼一下,顺便一看那些小菜”式的回忆性散文,当然力求做到既“诚实”又“亲切”。至于作者所力求的能不能真使读者也真正感觉到,当然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不过,这既在作者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那么也就暂且不去管它了吧!
徐家祯
1995年6月1日
写于斯陡林红叶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