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当我们谈论艺术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
2015 年我在逛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时,在博物馆商店买了他们那里仅有的两本中文书,一本是大都会博物馆的指南,另一本叫《艺术是……》,它关注了一个“世纪之问”——艺术到底是什么?它用两百多件馆藏艺术品给出了两百多个关于“艺术是什么”的“答案”,但是,它也意味着“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确定唯一的答案,艺术似乎并不容易使用理性的、学术的语言来定义。
这些年来,我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了一些艺术普及方面的事情。其实,我也经常在想,艺术吸引我们一次次走进美术馆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欣赏艺术的时候到底在欣赏什么?当我们谈论艺术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些什么?
我的解说并不学术,也不热衷于以学术的方式去研究和看待艺术,我总是觉得绘画和雕塑最本质的欣赏是观看和感受——既不是卷帙浩繁的艺术史,也并非大众喜闻乐见的八卦与故事,更不是它们在拍卖市场上的价格表现——尽管这些要素构成了它们作为艺术品的魅力,但这并不是艺术本身的魅力。艺术的面孔就是一个视觉形象(同理,音乐是“听觉形象”),通过光线进入瞳孔作用于人的头脑,再结合每个人不同的人生阅历和人文底蕴,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个性化的感受——这个感受可能是强烈的,也可能是淡淡的,可以是思索,也可以是共鸣,可能很美,也可能很丑,可能就是图解故事,也可能完全不知所云,带来的情感可以是伤感,也可以是喜悦,可以是愤怒的、激昂的,也可以是恐怖的、恶心的,还有更多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五味杂陈……这才是我们一次次走进美术馆,站在一幅画或者一个雕塑面前,观察、体味、微笑、流泪、冥思苦想、恍然大悟的真正原因。
做艺术普及,就是希望我们回到最原始、最基本的观看,回到最本质的感受,如同千千万万个最普通的观看者一样。
这里我想聊聊在艺术欣赏过程中存在的几个常见的误区。
一、艺术欣赏“知识化”
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晰,在大家的眼中都是去一个集纳了收藏品的建筑里,通过一件件实物(作品)来了解世界、了解文明,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方式也完全一样,所以在很多人眼中,会将两者的定位以及功用混为一谈——学习知识。
我个人觉得,与美术馆相比,博物馆的作用更强调“知识”,当然,很多文物其实也是艺术品,比如青铜器的纹饰、瓷器的色彩、兵马俑和佛造像等同于雕塑……但总的来说,博物馆是通过实物来传播知识、讲述历史、介绍文明。
美术馆的最主要功用并不在于提供知识,尽管欣赏艺术是要有些知识基础——比如艺术史的知识、对于色彩构图造型审美演变等方面的知识、创作者的生平、绘画技法的知识、从图像学的角度去索隐和探秘……这些知识,似乎知道些会更有利于欣赏(其实也未必)。但艺术作品欣赏的,并不是这些知识,获取了这些知识也不代表就欣赏了艺术,知识并不是艺术欣赏的必要条件。
很多人觉得学到了“知识”,似乎就完成了欣赏过程,讲起某个艺术品时,能说一堆,听起来似乎很有“干货”,看起来是“得到”了。而艺术的感受似乎变得不重要了,因为感受是千差万别的,也没有标准答案,个人有感受也不好意思说,怕“不对”被人耻笑;关键在于,感受通常很复杂,很难用语言表述清楚,说不清的东西似乎看不见摸不到,无法体现为“学习”的成果——“干货”,不能体现为“得到”了。
但艺术欣赏不是背书、考试、答题,我的个人观点是,如果没有感受,一切艺术知识的“得到”都是零,没有任何意义。
除了极少数艺术专业研究者和从事艺术工作的创作者之外,绝大多数的艺术欣赏者,并不需要使用跟研究者和创作者同样的视角和方法论。“欣赏”和“研究”是两条不同的路径,艺术史学习也应主要服务于欣赏,而不是钻牛角尖的学术考据。比如执着于哪个画家属于哪个流派或者风格,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意义。绝大多数画家并不是先定位自己属于哪个流派或者风格,才开始创作的;还有很多艺术家在艺术生涯中,不同的时期呈现出的风格也是迥异的。艺术史上归类的意义不过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切忌舍本逐末,走得太远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我在前文提到“似乎知道些知识会更有利于欣赏”的同时,还补了一句“其实也未必”——因为“知识”还存在一个重大的弊端,就是很容易形成“所知障”。也就是,你被你知道的“知识”和“干货”给干扰了、捆缚了,你失去了感受艺术的动力,也失去了感受艺术的“天真”,你抱着那些知识和干货以为自己拥有了“宝藏”,这让你反倒远离了艺术本身但你却浑然不觉。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句话并不适用于艺术,有时候“外行”因为没有“知识”和“技法”的困扰,反倒能对艺术产生更多的感受和共鸣,而“内行”却因为习惯于关注技法和知识,失去了感受它们的能力。
一切的一切,都要回到眼前,回到艺术品原作本身,回到观看。知识是要学一些的,但是它们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干货”是为欣赏服务的,它们都是你的奴隶,你不能变成它们的奴隶。
二、艺术欣赏“故事化”
围绕着一件艺术品本身,经常有很多故事可讲:作品绘画主题中包含的故事(尤其是宗教、神话、历史故事)、作品本身的创作故事、画家的趣闻逸事情史八卦、作品收藏传承的多舛命运故事(比如《蒙娜丽莎》被盗、《富春山居图》被烧)……所以介绍起艺术作品来,很难避免讲故事。
我也会讲,尤其是绘画主题涉及故事时,没办法不介绍一下,但坦率地说,我并不是很喜欢讲故事,一来我讲故事能力不强,二来以讲故事来替代欣赏并不符合我的价值观。现在有一种不太好的趋势是,大家用听故事来替代对于艺术本身魅力的探寻。爱听故事是人的本能,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故事当然是个喜闻乐见的形式。用故事做艺术普及的确有效,由此激发了相当多的人对于艺术的兴趣,把大家“忽悠”进了美术馆,应该说善莫大焉。
不过,故事的作用可能主要在于提高观看者的兴趣,但故事并不是观看本身。很多人觉得听了一堆故事、学了一堆知识,但是如何欣赏艺术还是“找不到北”;或者有些人听了故事就觉得自己“得”到了,对于艺术作品本身失去了探寻的兴趣,无意之中跑偏了。
不赞同“故事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故事极有可能不是真的。
一方面,故事是过去的事,很多都是很不可靠的传闻或者传记作者的主观想象和文字润饰,距离真相可能差之千里。如果故事不真或者不太真,那我们对于艺术的解读就有可能被严重误导,我们所感知的“艺术”,极有可能是那个故事的魅力,而非艺术品本身的魅力。
另一方面,故事有个天生的悖论,就是它的效果经常不是取决于它的情节,而是取决于它的讲述者。我认识一位口才极好的人,我跟他在同一个现场见证同一个事件,他讲起这个事儿来就会妙趣横生,而亲见同一个事情的我,则知道真相远没有那么有趣。后来我恍然大悟,他是通过细节上的拣选、局部放大和对于情节的“添油加醋”来使得故事生动的。“添油加醋”当然会让故事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但它越有趣,离真相就越远,我们以为自己欣赏了艺术,而实际上,我们只是欣赏了那个故事的“讲述”。至于事情的真相怎样,在热衷于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眼中,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效果(甚至是“笑果”)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对于过分有趣的“故事”,我会非常警惕里面的水分,换句话说,别被他们给忽悠了。
在艺术普及的领域,还有一种趋势,就是过分追求“有趣”——除了我刚才说的“添油加醋”强化故事性以外,还有的是在“遣词造句”上追求有趣,或者在“语气语态”上追求有趣。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有趣的东西才能博人眼球,好玩跟电影的“笑点”一样变成了刚需。于是,有些故事的讲述就开始没有节制地追求有趣,哪怕是非常感人的作品和作者,有人也会用“有趣”的方式来讲述和解读。
我听过一位教授做的普及讲座,老先生曾做过艺术史讲座,自然能深入浅出、活泼生动。但是那天讲到徐渭的《墨葡萄图》时,他说:有人问他,为什么葡萄都画成了一个个黑点?他回答说,因为画的是“葡萄干儿”。当时的会场是哄堂大笑。“葡萄干儿”的说法确实有趣,“笑果”显著。但是作为徐渭作品的爱好者,我感觉“葡萄干儿”的说法太过戏谑了。《墨葡萄图》是一幅表现绝望的画,而“葡萄干儿”是个美味吃食,《墨葡萄图》激发的是人心深处的“无力”和“无奈”,而哄堂大笑的“效果”则抹杀了那种深刻的感动。该活泼时要活泼,不该活泼时绝不能活泼,追求“有趣”也要有分寸。那天那个哄堂大笑让我觉得非常难过,这样的“有趣”是对艺术的误导,甚至是“亵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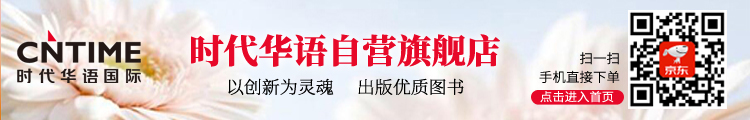








驴***者 2020-12-31 22:25:46
精品!强烈推荐吴老师的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