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公认的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1922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人专攻东洋史,1936年赴法留学。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后任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等客座教授。曾荣获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他的著述被广为阅读和引用,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等都是他的书迷。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东洋的近世》等。身后,《宫崎市定全集》共二十五卷出版,几乎包括汉学全部领域。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型态、文化性质、权力关系、政府组织各方面对汉文化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宫崎市定解读《史记》
- 书籍语言:简体中文
- 下载次数:5552
- 书籍类型:Epub+Txt+pdf+mobi
- 创建日期:2018-03-22 06:10:03
- 发布日期:2025-10-06
- 连载状态:全集
- 书籍作者:宫崎市定
- ISBN:9787508679938
- 运行环境:pc/安卓/iPhone/iPad/Kindle/平板
- 下载地址
内容简介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中国*部正史,它生动地描绘了古代中国的社会与人。《史记》诞生后,中国几乎没有能够*它的史书,评论《史记》几乎与评论中国的整个历史有着同等的价值。《史记》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它在日本也随着遣唐使传入后广为流传。经过六十年的钻研,宫崎市定从《史记》的成书到结构全面解读这部伟大的名著,著成这部*的《史记》入门经典。
在本书中,宫崎市定展现了他独特的《史记》解读法。他对于司马迁在体例上的变通赞赏有加,认为“体例的设立应当是为了记述的便利,如果因为体例的存在而受到束缚,无法从心所欲地下笔,那就是世界上*傻的事了。”对于《史记》的叙事手法,作者发现其中文学价值较高的篇目,都遵循着中国古代诗歌一般“起承转结”的结构,并且推测可能受到了古代戏剧形式“偶语”的影响。此外,本书中时常夹杂着作者对司马迁的简评,虽是只言片语,却生动风趣,尽显智慧。
在充分了解作者司马迁的人格与经历、《史记》的结构与风格之后,宫崎市定读出了《史记》中展现的真实的古代中国。那是一个如同古希腊、古罗马一般的古代市民社会。民众的主体,是居住在城郭里的自由民。他们每天早早地走出城门,在自家农田里辛勤劳作,日落时分回到城里休息。在这里,他们不再被一个词语或者几行文字所概括,他们是真正鲜活地存在过的人。
作者简介
编辑推荐
"★正确解读《史记》就是正确解读中国历史,读懂《史记》从本书开始。
★“汉学诺贝尔”儒莲奖得主、京都学派史学泰斗宫崎市定研读《史记》六十年经验结晶,借大师之眼读懂《史记》。
★问世38年长销不坠,文库本加印20次,畅销10余万册,日本人靠它读懂《史记》。
★仅有的分体例全面解读《史记》的著作,本纪、世家、表、书、列传逐一解读,阅读《史记》的*入门书。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南京大学教授张学锋联袂推荐。"
下载地址
序言
序言
我与《史记》的交往,大约已经有六十个年头了。最早是在旧制高中的时候,我曾读过一本名为《史记通鉴抄》的教科书。进入大学后,虽说硬着头皮一睹《史记》的真貌,但也没有到每天都要翻阅《史记》的程度。不过,在思考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必定会时常感觉到有参照《史记》的必要。
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时候,是打算将其写成一本包括当代在内的中国通史的。但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它也不过是作为中国通史一部分的古代史而已。他独特的史观,今天也无法直接运用。但《史记》作为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根本史料,这一点是不变的。可以说,正确解读《史记》就是正确理解中国古代史。
大约是刚从大学毕业的时候,友人从中国归来后向我询问道:日本有哪些研究《史记》的学者呢?我被他的问题难住了,日本很少有这样的文献学者,即便说研究《史记》,也多半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运用《史记》。这不如说是理解《史记》的捷径,所以日本的研究方法与中国有着各自特色。
关于《史记》,我至今写过相当数量的论文,而且可以自豪地说,我不止一两次地发现了以往研究方法所没能读懂的问题。此次在岩波新书中解读《史记》,我心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案,正在为选择哪一种而苦恼。
一种是基于我已经发表的论文加以衔接,以简单易读的面貌呈现给读者。我们无法指望学术论文能有太多人去阅读,所以迎合着新书做一些改写也绝不是没有意义的。
另一种是索性重新构思,以尽可能不使用已发表的论文作为方针,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起稿。新书就像一个新的容器,如果盛放的不是原本就为此准备的材料,就无法保证每一个角落都能严丝合缝。不过是否能够赶上时间的限制,这也是一种冒险。
但实际动笔后才发现,这样的犹豫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自己所写的内容,最终自然就倾向了没有使用过的材料。与此同时,我也不得不意识到新书要便于读者阅读,记述上自然无法与学术论文相比,到处都会有不充分的地方。阅读本书的读者们如果也有同样的感觉,请进一步阅读书后刊载了标题的我的相关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形成独立的关于《史记》的看法。
昭和五十四年(1979年)二月
宫崎市定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史记》的读法——我们曾经怎样读《史记》
第二章 正史之祖——纪传体的创立
第三章 本纪——中国的辩证法
第四章 世家——政权割据的力学
第五章 年表——历史可以追溯到多远
第六章 列传——古代市民社会的人们
作者《史记》相关论文一览
《史记》简要年表
《史记》中的女性
解说(吉川忠夫)
短评
-
JNA 2018-03-07
读完漠然好一会,大脑空白片刻,这是个哀伤的过程,无论是宫崎爷爷还是历史中的司马迁,他们在重叠,宫崎读出了司马的自由意志,这才是历史层层重幕也无法掩盖的东西。而宫崎爷爷的解读我给予全五星的书评,除了仁这部分我还不敢苟同,至少我要自己思索,余下全部认可。并且对列传的评论尤为赞同。非常好看的一本书
-
Fitzcarraldo.L 2018-01-11
老吏断狱,言浅意深,以“起承转结”之中国辩证法思维为太史公继春秋之志与治史法门张目,“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装帧虽精良,但小五号字体加1.5倍行距反阅读,扣一星,不是宫崎先生的锅…
-
不许无聊 2018-03-11
对不知《史记》为何物,或想大致了解《史记》的人有帮助。如果已经看过吕世浩的史记,就别浪费钱了。
-
icarus 2018-02-22
行距这么大,字号这么小,我猜编辑是不读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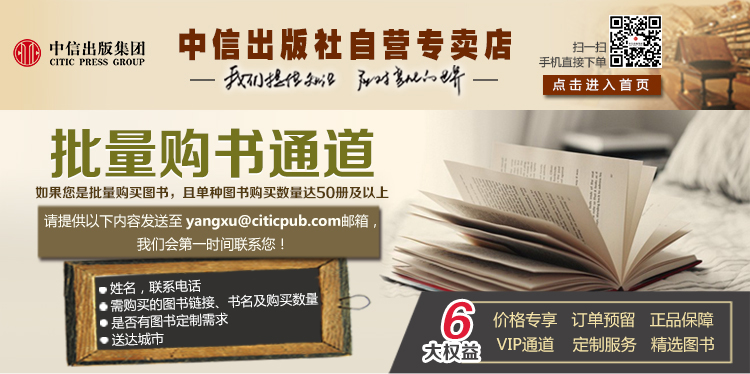
那希索斯 2018-02-24
老先生对中国、日本传统的史记研究方法都不太满意,他提出的观点颇为新颖:“鲁国拥有着如同古希腊的雅典一样的地位”、“孔子说的仁,有时候翻译成自由最为通顺”等等。很好看,杨照写论语等等典籍的方式,与此也有异曲同工之妙。